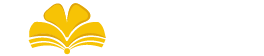傅正国的瞳孔猛地一缩。
他当然没忘。
这是傅承安在发病前,瞒着所有人做的财产转移,也是傅家至今不敢把我直接扫地出门的唯一原因。
“你想用这个威胁我?”傅正国声音里带着冷意。
“不是威胁。”我摇摇头,“是提醒。”
“提醒您,我现在是傅承安法律意义上的唯一监护人。他现在生病,那么作为配偶,我有权替他做决定。”
“这七天直播,就是我这个监护人,为他选择的特殊治疗方案。”
“谁敢中断,就是意图谋夺他的财产。”
我把话说得很重。
客厅里,死一般的寂静。
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。
他们想不通,那个一向在傅家温顺、隐忍的林婉,怎么会突然长出了一身刺。
傅承雅气得浑身发抖,“你……你简直不可理喻!”
婆婆指着我的鼻子,“反了天了!真是反了天了!”
我懒得再跟她们纠缠,转身准备上楼。
“林婉。”
傅正国叫住我。
我停下脚步,没有回头。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他的声音里,多了疲惫和探究。
我回过头,冲他笑了笑。
“我想干什么,七天后,您不就知道了?”
说完,我径直上了二楼,反锁了房门。
房间里很安静,我能听到自己沉稳的心跳声。
我打开电脑,上面是祠堂的监控画面,分成了九个不同角度的格子。
这是我自己找人装的,比傅家那个只对着正门的摄像头,要全面得多。
画面里的傅承安,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,一动不动,像一尊雕塑。
我把其中一个对着他侧脸的画面放大。
他的嘴唇在无声地翕动,重复着两个字。
“快逃。”
我的眼眶有些发热。
接下来的两天,风平浪静。
傅家人似乎接受了我的“治疗方案”,没再来找我的麻烦。
他们只是派人守在祠堂门口,也守在我的房门口。
一日三餐,会由佣人送到门口。
我成了这个家里的另一个囚徒。
我不在乎。
我所有的时间,都用来盯着监控。
傅承安每天除了必要的吃饭喝水,几乎都在长跪。
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下去。
每天凌晨三点,当所有人都睡着了,祠堂外看守的人也最困倦的时候,他会抬起左手,用小指,轻轻敲击三下自己的膝盖。
我也会在我的房门内侧,敲击三下,作为回应。
我知道,他能听见。
这栋大宅的隔音很好,但我们房间的通风管道,是相连的。
到了第四天,事情起了变化。
婆婆支开佣人,亲自把参汤端了进去。
“承安,我的儿,你受苦了。”
“快,把这个喝了,妈亲手给你炖的。”
画面里,傅承安抬起头,眼神空洞地看着她。
他没有接。
婆婆的耐心很快耗尽。
“你喝不喝?为了那个女人,你连妈的话都不听了?”
“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!人不像人鬼不像鬼!”
“都是林婉那个贱人害的!”
傅承安的嘴唇动了动,发出沙哑的声音。
“是……我不孝。”
婆婆愣住了,随即脸上露出狂喜。
“你知道就好!你知道就好!”
“快,喝了汤,跟妈回家,咱们不管那个疯女人了。”
她把碗凑到傅承安嘴边。
我的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我知道那碗汤里有什么。
和三年前,傅承安的大伯,傅正业喝的那碗,一模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