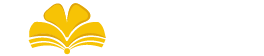他的话,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他们记忆的闸门。
我的灵魂泛起一阵苦涩的涟漪。
我没想到人死了还要被造谣。
那一次,根本不是什么社会青年,而是陆清远自己网购了一大堆健身器材,却懒得去小区门口的驿站搬,便命令我去。
我拖着沉重的箱子往回走,不小心撞到了几个正在路边休息的建筑工人,对方看我瘦弱,还好心帮我抬了一段路,仅此而已。
可这一幕,却被陆清远添油加醋地描述成了我与黑社会勾结的证据。
那天晚上,我被罚不许吃饭,跪在客厅里反省。
父亲骂我不学好,丢了陆家的脸。
母亲说我骨子里就带着下三滥的基因。
现在,旧事重提,他们脸上的厌恶又浓重了几分。
“我就说他不干净!”母亲咬牙切齿,“从福利院出来的人,能有什么好东西!为了钱,什么事做不出来?”
“真是丢人现眼!”父亲重重地拍了一下方向盘,“等会儿到了,确认是他,就赶紧处理掉,别让外人知道!”
姐姐陆晚晴则靠在窗边,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,声音冰冷:
“他最好是真的死了,一了百了。省得再回来给我们陆家抹黑。”
他们一路咒骂着,给我编织了无数个肮脏的罪名。
仿佛这样就能减轻他们即将要去认领一具尸体的心理负担。
他们已经提前预设了我的罪有应得,准备好去面对一个不知好歹、自甘堕落的儿子的结局。
终于,车子在警局的法医中心门口停下,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。
“家属请做好心理准备。”法医的声音毫无波澜,“死者被发现时,情况……不太好。”
一张不锈钢停尸床上,覆盖着白布。
随着法医将白布缓缓揭开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
我枯瘦如柴,仿佛所有的血肉都被抽干,只剩下一层皮紧紧地包裹着骨头。
长期营养不良让我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蜡黄的病态,上面布满了青紫色的冻疮。
而最可怖的,是我的四肢和脸颊上,那些被野狗啃食过的、深可见骨的伤口,残破不堪。
“啊——!”
母亲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,双腿一软,瘫倒在地。
父亲的身体也重重地晃了一下,下意识地伸手扶住墙壁,他那张总是充满威严的脸上,第一次出现了龟裂般的震惊与空白。
姐姐则像被施了定身术,僵在原地。
她的瞳孔急剧收缩,死死地盯着我那张残破的脸,嘴唇无声地开合着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他们预想过无数种可能,却唯独没有想过,我会是以这样一种凄惨、卑微、甚至可以说是惨绝人寰的方式死去。
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,陆清远的声音突兀地响了起来,尖锐而刻薄,试图划破这令人窒息的真相。
“天哪……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……”他先是夸张地捂住嘴,眼中却不见丝毫悲伤,只有一丝一闪而过的慌乱。
随即,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,用一种恍然大悟的语气,继续他那恶毒的诋毁:
“我……我知道了!他肯定是跟外面那些人鬼混,学着吸脏东西了,把身体搞垮了,不然怎么会瘦成这样?”
“他肯定是没脸见人,又没钱买毒品,才躲出去自己等死的!”
他转向已经呆滞的父亲和姐姐,急切地说道:“爸,姐,你们看,我就说他不学好吧!这种人,死了也是活该!我们赶紧把他带走,找个地方烧了吧,太丢人了!”
“要是让记者知道了,我们陆家的脸往哪儿搁啊!”
他的话,像一把把刀子刺向了在场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的耳朵。
一直沉默的警察终于听不下去了。
“这位先生,我不知道你和死者有什么深仇大恨。”
“但是请对死者保持最基本的尊重。”
“根据我们的调查,死者死亡时间超过一周,死因是极度饥饿、受冻引发的器官衰竭,除此之外,没有你说的任何原因,不要造谣。”
“这起非自然死亡抛尸的刑事案件我们会进一步调查,请各位配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