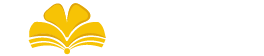他没有回答我的话,而是淡淡地啐了一口血沫。
“这帮畜生。”
他低头看着我,沾着血的手指有些凉,但还是小心地避开了我胳膊上的针眼。
“你是谁家小孩?”
我没有回答,只是把脸埋在他的西装上,眼泪无声地滑落。
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流泪,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为那个被献祭的姜阮哭丧。
那个天真地以为只要乖巧懂事就能换来父母垂怜的小女孩,已经死在了衣柜门口,死在了这张手术台上。
现在活着的,只是一个想要抓住救命稻草的努力活下去的孤魂野鬼。
鬼使神差地,我伸出瘦弱的胳膊,搂紧了男人的脖子。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,带着破碎的哭腔,喊了一声。
“爸爸。”
抱着我的男人身体明显僵了一下。
他周身那股骇人的杀气似乎也因为我这声称呼,停滞了一瞬。
我能感觉到他的肌肉紧绷着,似乎随时会把我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丢出去。
我只能赌,赌他对我这个孩子还有一丝怜悯。
良久,他没有推开我。
一只大手落在了我的后背上,略带无奈地,一下一下地轻拍着。
动作生疏又僵硬。
“也是个可怜的。”
他的声音低沉,在我耳边响起。
“但是,做我傅辞的女儿,可不能哭鼻子。”
傅辞。
我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我立刻止住了哭声,只是依旧把脸埋在他怀里,像一只找到了巢穴的幼兽。
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
他可以是我新的“爸爸”,但前提是,我得听话,不能软弱。
傅辞抱着我,转身走出了这个白色的房间。
门外,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穿白大褂的人,血流了一地,空气中的血腥味更浓了。
我没有害怕,反而有种释然的快感。
傅辞目不斜视地从他们身上跨了过去,皮鞋踩在血泊里,发出黏腻的声响。
他的手下跟在身后,恭敬地低着头,大气都不敢出。
我被他抱上了一辆黑色的车。
车里很暖和,和他略带凉意的怀抱截然不同。
一个手下递过来一条干净的毛毯,傅辞接过,把我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,只露出一颗脑袋。
“回庄园。”
车子平稳地驶出,将那座金碧辉煌的人间地狱甩在身后。
我靠在傅辞怀里,药剂的副作用让我昏昏欲睡,但我强撑着不肯闭眼。
我怕这是一场梦,梦醒了,我又回到了那张冷冰冰的手术台上。
傅辞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安,他那只大手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后背,一下一下,有节奏地轻拍。
“睡吧。”
他淡淡地开口。
“以后没人敢动你了。”
他的声音像是带着某种魔力,让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,沉沉地睡了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