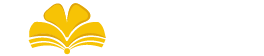中秋灯会时,妹妹与我走散。
不久后,巷子里发现了一具无头少女的尸体。
母亲恨毒了我,把我关在祠堂为妹妹诵经祈福九九八十一天。
后又叫人将我卖到烟花柳巷,让我为妹妹赎罪。
她吩咐那楼里的人,只叫我接最低贱的客,留一口气便成。
那鸨母拿钱办事,安排给我的客人都是有特殊癖好的。
我日夜被折磨,染了花柳病也不得医治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了孩子,也不知什么时候流了。
直到某个客人手下重了,我死在了床上。
鸨母命人用草席将我一卷,随手丢进了乱葬岗。
直到大半年后的除夕夜,妹妹回来了。
1
我死的时候,身上正压着一个满身酒气的男人。
他是我今晚的第三个客人,也是最后一个。
他说他最喜欢听骨头断裂时清脆的声响,那比任何乐曲都动听。
我的左臂,就是刚刚被他以一个诡异的角度,伴随着他满足的叹息,生生折断的。
剧痛像烧红的烙铁,猛地烫穿了我的神经,随即又像潮水般迅速退去。
只剩下一种麻木的、彻骨的冰冷。
我能清晰地感觉到,生命正从我这具早已千疮百孔的身体里,一丝丝、一缕缕地抽离。
男人在我身上酣畅淋漓地发泄完,心满意足地起身。
他肥硕的手指捏起桌上的一锭碎银,又嫌恶地丢了回来,砸在我脸上,冰冷坚硬。
“没用的东西,才玩一下就跟死鱼一样,没气了。”
门吱呀一声被推开,鸨母扭着她那水桶般的腰肢走进来,兰花指捏起那点银子,在嘴里吹了吹。
又伸出穿着绣花鞋的脚,狠狠踢了踢我一动不动的腿。
见我半点动静没有,她俯下身,探了探我的鼻息,脸色瞬间一白,咬牙低声叫来小厮。
“草席卷了,扔去城西的乱葬岗,别叫人看见了。”
见我被拖出去,她咬着唇嘀咕:“左不过的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命丫头,应得没人管。”
“下辈子投个好胎去享福吧。”
投个好胎吗。
如果真能如鸨母所言便好了。
意识模糊间,我的魂魄仿佛被拉扯着,回到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中秋夜。
灯火如龙,人潮如织。
我紧紧牵着妹妹明珠的手,她的手又小又软,我生怕一个不留神,她就会被这汹涌的人潮冲散。
可一转眼,一个卖面人的摊子吸引了她的目光,她指着一个穿着粉色罗裙的小面人,欢呼雀跃。
“姐姐,我要那个,我要那个!”
我不过是松开手,去钱袋里掏铜板的片刻,再回头时,那抹熟悉的身影就不见了。
我疯了一样地在人群中寻找,一遍遍地喊着她的名字,喊到嗓子嘶哑,喊到喉咙里泛起血腥味。
直到深夜,巡夜的官府衙役才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。
不久后,城南的一条暗巷里,发现了一具无头少女的尸体。
那尸身穿着和明珠走失时一模一样的藕粉色罗裙,裙摆上还绣着她最喜欢的蝴蝶。
而后我便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一段岁月。
我在祠堂跪了九九八十一天,仅靠心善仆人每天给的一碗米汤度日。
从祠堂出来的那天,我成了春风渡里最廉价的妓女。
我的客人,不是年过古稀的老叟,就是有各种残忍癖好的变态。
他们在我身上发泄着最原始的兽欲,用鞭子、用烙铁、用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刑具。
我日夜被折磨,很快就染上了花柳病。
身上开始出现溃烂的红疮,疼痒难耐。
可鸨母说,这是我母亲交代的,不准医治。
后来,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怀了孩子。
我甚至不知道那是我哪个客人的种。
在一个雨夜,一个喝醉的嫖客嫌我伺候得不尽心,将我从床上踹到地上,用脚一下一下地猛踹我的小腹。
我蜷缩在地上,感觉身下一片温热的黏腻。
一滩血,从我腿间蜿蜒而出。
那个还未成形的孩子,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没了。
自此我便没有了盼头,直到刚刚,终于结束了我这浮萍般的一生。
明珠,姐姐来陪你了。
这罪,我终于为你赎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