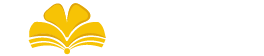拘留所的日子比想象中平静。
一日三餐,定时熄灯。
除了自由,什么都有。
陆凛没有再来。
大概是被我那句“姐姐的命”镇住了。
也好,我需要时间。
第三天,我开始咳嗽。
起初只是喉咙发痒,后来,咳得撕心裂肺。
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。
同屋的人被我吵得睡不着,骂骂咧咧。
我捂着嘴,蜷缩在角落的硬板床上,咳得浑身发抖。
一股铁锈味涌上喉咙。
我摊开手掌,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,看到一抹暗红。
血。
狱警发现了我的不对劲。
他们冲进来,打开灯,看到我惨白的脸和手心的血。
一阵兵荒马乱。
我被紧急送往医院。
躺在移动病床上,看着头顶飞速后退的日光灯,我竟然感到一丝解脱。
终于,要来了吗?
在医院,给我做检查的,是我的主治医生,李医生。
他看着最新的CT报告,手都在抖。
“林霜,骨转移三期,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?”
他痛心疾首地看着我。
“再不住院系统治疗,神仙也救不了你!”
我没看他,转头望向窗外。
外面是灰蒙蒙的天,和一栋栋冰冷的建筑。
我的花店,我的“霜降”,就在不远处的街角。
现在,应该只剩下一片废墟了吧。
我收回视线,看着李医生,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
“李医生,你搞错了。”
“这张判决书,不是我的催命符。”
我撑着床沿,慢慢坐起来。
“是我的起跑枪。”
……
我没听李医生的劝告,办了出院。
我没有回家,也没有去那片废墟。
我打车去了西郊的墓园。
天阴沉沉的,下起了小雨。
我撑着一把黑色的伞,一步步走上台阶。
在最高处,找到了姐姐的墓碑。
照片上的她,笑得温柔又恬静。
我伸出手,想擦掉碑上的雨水,指尖却触到一片冰冷。
我在墓碑后面一个不起眼的凹槽里,摸索了一阵。
取出一个用防水袋层层包裹的铁盒子。
打开盒子,里面是一本日记。
是姐姐的遗物。
我撑着伞,蹲在墓前,一页一页地翻看。
日记里,记录了陆凛父亲的陆氏集团,生产的那批劣质医疗器械,是如何让她一个原本只是小手术的病人,一步步感染,恶化,最终走向死亡的。
也记录了陆家是如何用权势和金钱,打压我们,威胁我们,逼疯了我们的父母,让他们在绝望中相继离世。
最后一页,是姐姐用尽力气写下的血字。
“霜霜,活下去,为我。”
雨水打湿了日记本,字迹晕开,像一道道流血的伤口。
我再也忍不住,伏在冰冷的墓碑上,放声痛哭。
哭声被雨声掩盖,无人听见。
哭了不知多久,我慢慢站起来。
擦干眼泪,将日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回铁盒,贴身藏好。
我拿出手机,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。
电话很快被接通。
“林霜,你又想耍什么花样?”陆凛的声音很不耐烦。
我没有理会他的质问,“陆凛,准备好,游戏正式开始。”
“我会让你亲眼看着,你所珍视的一切,如何像我姐姐的生命一样,一点点,化为灰烬。”
说完,我挂了电话。
风吹过耳边,像姐姐在低声呜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