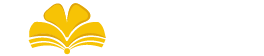酒坊开张第一天,没有客人。
第二天,还是没有。
娘就坐在门口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街口。
我肚子饿得咕咕叫,可我不敢吭声。
屋里还飘着酒糟的余味,那味道钻进鼻子,更饿了。
我的眼光,老是不自觉地往那扇朱红大门上溜。
有人说,爹就是从那扇门里,被砍断手脚塞在酒坛里抬出来的。
我还记得爹身上的酒香,暖烘烘的。
他说要教我酿酒,我们家的手艺,传男不传女,可我是他唯一的孩子。
我以为,日子就会这么过下去。
在酒坊里,听着爹的声音,闻着粮食发酵的香气,一直到老。
爹活着的时候,娘是不出后院的。
她那张脸,太招摇。
有次布行的掌柜来打酒,眼睛黏在娘身上,被我爹抄起扁担赶了出去。
爹常说:“咱们就是靠手艺吃饭的,平平安安比啥都强”
他的酿酒手艺再好,也从不主动宣扬,客人都是口口相传慕名而来。
我爹这辈子,唯一惹眼的一次,就是被顾国公府的人请走。
那时爹犹豫了很久,最后还是不敢不去。
临走前,他摸着我的头说:
“这次赏钱多,给你娘扯块新料子做衣裳,再给小七买支顶好看的珠花。”
早知道……我什么珠花都不要了。
我只要爹。
同乡大叔趁夜,用驴车从乱葬岗把爹拖了回来。
坛子是咱家装酒的坛子。
爹在里面,手脚都没了,血肉模糊。
大叔红着眼,牙缝里挤出几个字:都是那个宠妾!
后来,我知道了那个女人的名字。
许锦瑟。
顾国公顾长渊心尖上的人。
一个边关来的妓子,听说舍命救过顾长渊,他就把她当眼珠子疼。
大人们在墙角悄悄说,那女人对顾长渊放过话:
“我救你的命,你就是我的人!名分那玩意儿我不要。”
“可你要是敢看别的女人,我先划了她的脸!”
顾长渊呢,非但不怕,反而就喜欢她这股泼辣劲儿。
为了她,他什么都肯做,连明媒正娶的夫人裴氏,都扔在后院不管不问。
许锦瑟见了我爹,问:“你很会酿酒?”
我爹正要躬身回答,她却不耐烦地打断:
“别说废话。我问你,能不能酿出一种酒,喝进嘴里没酒味,醉了也不知道自己醉了?”
我爹没听懂,陪着笑脸:“夫人,既是酒,怎会无味。”
“废物!”许锦瑟眼中满是疯狂,就叫人堵了爹的嘴。
砍断手足塞进了酒坛。
“既然酿不出我要的酒,你就自己变成酒吧!”
顾长渊听说了这事,只是捻了捻手里的佛珠,叹了口气:
“罢了,锦瑟就是心思重,也怪那酿酒的不会看眼色,多烧些纸钱抚恤吧。”
同乡把这些话学给我娘听,她一声没吭。
只是守着爹残缺的尸身,手一遍遍地抹过,很轻很温柔。
“好好睡一觉,睡醒了,我还做你的妻。”
丧事办完,我在爹的包袱里翻到了一朵珠花。
我攥着它,对娘说:“娘,我想去京城。”
娘看着院里还没扫干净的纸钱灰,看了很久很久。
“去,当然要去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