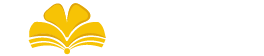沈卿棠还没反应过来,就听到祁晏的下一句:
“八年里我就没见过你虾仁过敏,故意找茬也要找个好点的理由。”
心仿佛被针尖刺了一下,有些痛。
她想笑。
“八年了,你难道都不知道我虾仁过敏吗?”
“啪”的一声。
沈母的巴掌狠狠落到她的脸上,厌恶地看向她:
“你还在狡辩!你是我的孩子!你过不过敏难道我不知道吗?!”
沈母当然知道,毕竟沈卿棠八岁下山第一次过暑假,就是被沈月眠骗着吃下虾仁,脸肿成了猪头。
可这并不妨碍她维护小女儿。
沈卿棠被打得偏过头去,身侧的手紧握成拳。
下一刻,又被祁晏一把掐住下巴,男人眯起眼,显然听信了沈母的话:
“你果然是装的。”
“惹了眠眠,你总该知道下场。”
保镖应声而来,将她扔到了庭院中,强行压制着跪在地上。
庭院里冰天雪地。
她穿得单薄,膝盖跪在大理石砖上硌得生疼,可却动弹不得,只能被保镖摁着,任由刺骨的寒风穿透骨髓。
眼眶微微湿润,因为委屈,更因为祁晏的薄情。
直到半夜,她才被松开。
别墅里,天花板硕大的吊灯被关闭,只有一盏小夜灯亮着。
小夜灯下,沈月眠在药箱里翻找。
见到她,沈月眠将手里的药片喂进嘴里,嘴巴动了动。
“你在吃什么?”沈卿棠问。
问句被冷厉的声音压住:
“你对眠眠做了什么?”
没来得及回答,她的肩被男人大力抓住:
“我再问一遍,你对眠眠做了什么?她怎么会半夜起来吃药?!”
沈卿棠张了张嘴,牙关冷得发颤:
“我什么都没做。”
可她声音的颤抖,几乎是一瞬间就被男人定下了死刑。
“晚饭时故意说自己对虾仁过敏,刚被放进来,又想着开始欺负眠眠了是吗?”祁晏毫不留情掐住沈卿棠的脖颈:“沈卿棠,我为什么从前不知道你这么恶毒?!”
沈卿棠涨红了脸,拼命拍打脖子上的手。
快要窒息之前,祁晏厌恶地扔开了她。
寂静声中,药片锡箔纸的声音接连响起。
紧接着,就是一大把胶囊塞进了她的嘴里。
“喜欢撒谎自己过敏是吗?”
“那不多吃点过敏药怎么行?”
夜色中的声音透露出生吞活剥的意味。
还未来得及吞下,又是一把过敏药塞进喉咙。
一次接着一次,直到干涩的胶囊黏在她的食道中,呛得她不停地咳嗽,祁晏才收了手。
“再有下次,我不会轻易放过你。”
胶囊卡在喉咙里,沈卿棠止不住地干呕,猛咳。
生理性的泪水落在地上,沈卿棠分不清有几滴是发自真心的。
三番两次,不听解释,就笃定她是错的。
明明已经决定放下对男人的感情,为什么心还是会发出尖锐的痛。
身体只剩刺骨的冷,痛的感官反倒延迟几分,等她察觉到小腹猛烈的痛时,便直直晕了过去。
再醒来,就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。
手背扎着针,吊瓶正一滴滴往下漏液。
沈卿棠下意识抬起手,被一双温暖的手按住。
“别动,医生说你发高烧,还食物中毒,吊瓶还有几瓶没挂完。”
祁晏眼神落在沈卿棠身上,视线是罕见的平和。
沈卿棠别过眼,看着窗外的云。
声音在耳畔响起:
“昨晚的事是我误会你了,眠眠在吃健胃消食片,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报复你。”
“不过你不该骗眠眠说你虾仁过敏,她昨晚很伤心……”
“祁晏,”沈卿棠提不起兴致争辩,便打断了他:“做完化验的血应该还有吧,你让人查一查我的过敏原,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撒谎了。”
空气安静了一会儿。
“好,我去查。”
一阵突兀的铃声响起:
“阿晏哥哥,我的指甲被我剪丑了,怎么办呀呜呜……”
毫不犹豫地,祁晏向大门走去。
身形停顿了一下,他转头,对着沈卿棠颔首:
“公司有事要忙,等忙完了给你带松花糕。”
沈卿棠不期待他的松花糕。
事实也证明,她的不期待是正确的。
自那以后,整个住院期间,再也没人来过。
直到出院的那天,突然冲上来了一群保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