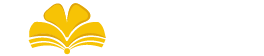话音落下,我不再看他脸上错愕的神情,径直走向卧室。
我拉开床头柜最底层的抽屉,从最深处摸出那个陈旧的针包。
打开的瞬间,里面密密麻麻的银针反射出森然的冷光,映着我没有温度的眼。
其中几枚早已从中断裂。
顾远征的目光跟过来,扫过那些残针,眼神里尽是无法理解的困惑。
我将针包紧紧攥入掌心,粗糙的布料硌着皮肤,带来一阵清醒的刺痛。
我转身就走,没有半分留恋。
经过他身边时,一阵熟悉的、淡淡的皂角香钻入鼻腔。
那是他从部队里带回来的习惯,用最简单廉价的皂块,洗去一身的汗味与尘土。
曾几何时,我迷恋这种干净利落的味道,将脸埋在他胸口,就能获得全世界的安宁。
如今再闻到,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。
“谢知念!”
他猛然在我身后出声,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急躁。
我脚步未停,甚至没有丝毫的迟缓。
“你以后……”
他的声音艰涩地传来,带着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迟疑,“有什么打算?”
我推开门,门外的风吹起我的发丝。
“活下去。”
我没有回头,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,任由它消散在穿堂风里。
“离你远远地,活下去。”
“砰”的一声,厚重的木门在我身后关上。
那声巨响,震落了我两世积攒的尘埃与执念。
我走出军区大院,午后的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下来,暖得有些不真实。
我眯起眼,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混合着青草与泥土气息的空气。
自由。
真好,我还活着。
我离开后的第三天,顾远征开始觉得不对劲。
家里空荡得可怕。再也没有人会在他深夜回家时,为他留一盏灯,端一碗热汤。
也没有人会在他伏案工作时,悄无声息地为他披上一件外衣。
过去那些他瞧不上的日子,真没了,才发觉心里空了一大块,有种烦躁感正一点点啃着他。
他只当这是不习惯。
余雅娴很快搬了进来,处处学着我的样子,想给他一个家。
可她做的饭菜,总不是他惯吃的味道。
她收拾过的房间,他也总找不到随手放的文件。
更要命的是,他的旧伤又犯了。
那疼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,又酸又麻,赶上阴雨天,更是折磨得他整夜睡不着觉。
“远征,是不是又疼了?我给你揉揉。”
余雅娴一脸心疼,手搭上他的肩膀按了起来。
她的手法很标准,是护士学校里教的那套,温柔,却像隔靴搔痒。
那点力道根本碰不到痛处,更别说止住那钻骨的疼了。
顾远征烦躁地一把推开她:“没用!”
他猛然想起我。
在我走前,每当他疼得受不了,我就会拿出那个针包,用细长的银针在他背上、腿上扎几下。
起初他很抗拒,说那是乡下人的歪门邪道。
可每次扎完,那要命的疼就散了,换来一身轻松和睡意。
他一直以为,那不过是心理作用。
现在才发觉,恐怕不是。
“雅娴,”他声音沉沉地问,“当初在医院,你到底是怎么给我做康复的?”
余雅娴的脸僵了一下,随即挤出个笑:“就……就是我自创的按摩法啊。我不是说过吗,能刺激神经再生……”
顾远征没吭声,就那么定定地看着她,看得余雅娴心里一阵发慌,嘴角的笑也僵了。
他没有再问下去,但怀疑的种子,已经种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