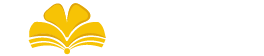我被赶出了家门,像一条丧家之犬。
我身上除了怀里高烧不退的女儿,一分钱都没有。
顾明轩追了出来,手里拿着一份文件,甩在我脸上。
“向晴,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。”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,“净身出户,另外,再签一份自愿放弃女儿治疗的声明,就算是你给我弟结婚的贺礼了。”
我看着他,这个男人,已经不是人了,是魔鬼。
我没有哭,也没有闹,只是冷冷地看着他,一字一句地问:“顾明轩,你就不怕午夜梦回,女儿来找你索命吗?”
他被我的眼神看得一哆嗦,随即色厉内荏地吼道:“你少废话!赶紧签!不然你和你这个赔钱货,都别想好过!”
我捡起地上的协议,签上了自己的名字,扔到了他的脸上。
“滚。”我只说了一个字。
我抱着滚烫的安安,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。夜色深沉,城市的霓虹灯刺得我眼睛生疼。
最终,我走进了医院,坐在急诊室外冰冷的长椅上。安安在我怀里昏睡着,小脸烧得通红,呼吸微弱。护士递来一张催款单,上面鲜红的数字,像是在嘲笑我的无能。
我第一次,感到了真正的走投无路。
我该怎么办?去偷?去抢?还是抱着我的女儿,从这医院的顶楼一跃而下?
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,我甚至能闻到死亡的气息。
就在我神思恍惚之际,一个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墨镜的保镖,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面前。
他像一座山,挡住了惨白的灯光,也挡住了我所有的视线。
他没有说话,只是递给我一张黑色的名片,质地坚硬,上面用烫金的字体印着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。
傅承砚,地址是本市最顶级的富人区,一个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地方。
我警惕地看着他,沙哑着嗓子问:“你是谁?想干什么?”
保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,不带任何情绪:“傅先生说,三年前,在一个暴雨的深夜,您在城西的废弃工厂,给过他一个面包。现在,他还您一份恩情。”
三年前?暴雨?面包?
零碎的记忆碎片在我脑海中拼凑起来。
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,我心情不好,独自开车去郊外散心,突降暴雨,车子抛锚。
我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门口躲雨,看到一个男人浑身是血地倒在角落里,狼狈不堪,奄奄一息。
我当时吓坏了,但看他不像坏人,出于一丝怜悯,我将车里唯一一个还没吃的面包,放在了他身边,然后就趁着雨小,跑了。
我从没想过,三年前那一个微不足道的善举,竟然会在我最绝望的时候,得到回应。
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打车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。
我被保镖带进了一间书房,见到了傅承砚。
他坐在轮椅上,脸色苍白,但一双眼睛却像鹰隼般锐利,仿佛能洞穿人心。
他没有多余的废话,直接让助理推过来一份文件。
“我救你女儿,你嫁给我,为期三年。”他的声音清冷,没有温度。
我愣住了,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。
“为什么?就因为一片面包?”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他没有回答,只是抬手指了指墙上的一幅油画。画上的女人,穿着白色的长裙,在阳光下微笑,那张脸看着有些熟悉。
傅承砚的助理在我耳边低声解释:“傅老先生病危,家族股权动荡,傅先生需要一场婚姻来稳定局面。”
我明白了。我只是一个帮他稳住家族的工具。
我低头看着怀里气息微弱的女儿,她的小手无意识地抓着我的衣襟。
尊严、爱情、自我……在女儿的生命面前,这些都变得一文不值。
我拿起笔,在那份名为“婚姻协议”的卖身契上,签下了我的名字——向晴。
我不在乎成为谁的工具,我只要我的女儿,活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