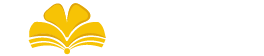从集市回来后,我病了一场。
不算严重,就是发了点低烧,浑身没力气。
周建军象征性地来看了看,留下句“好好歇着”,就又忙着去照顾隔壁了。
或许在他看来,嫂子一个人带着孩子,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比我这个正牌妻子的病痛重要得多。
我躺在炕上,烧得迷迷糊糊,心里却异常清醒。
指望他?下辈子吧。
不,下辈子我也不想再遇见他了。
既然他要换个活法,那我也换。
我的活法,就是离开他,为自己活。
病好后,我不动声色地为自己铺路。
我知道,在这个年代,一个女人想离婚,想独立生活,有多难。
但我有上辈子的记忆,我知道未来几十年的大概走向。
这是我最大的优势。
我开始留意村里和镇上的一切信息。
我知道,很快政策会松动,允许个体经营。
镇子南边那片荒地,几年后会建起一个大市场。
我们村后山上的某种不起眼的药材,将来会变得很值钱。
我需要钱,需要启动资金。
我把母亲偷偷给我的那点鸡蛋,还有我陪嫁时带来的一点私房钱,都小心地藏了起来。
我更努力地挣工分,不是为了这个家,是为了我自己。
我还利用去镇上赶集的机会,偷偷观察那些已经开始在路边摆摊的人。
卖针头线脑的,卖自家编的筐子的,卖烤红薯的……
我在心里默默盘算着,什么是我能做的,风险最小,又能快速积累一点资本的。
周建军对我的变化毫无察觉。
他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冷淡,但只当我是闹脾气,还在因为上次集市的事情还在生气。
他甚至觉得,这样更好。
我不吵不闹,安安静静地干活,他就能腾出更多精力去照顾嫂子。
他完全沉浸在自我感动的牺牲和补偿里。
一天晚上,他又去了隔壁,很晚才回来。
我假装睡着了,听到他轻手轻脚地摸到炕上,然后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。
那声叹息,像一把钝刀,慢慢割着我的心。
但我没有哭。
眼泪,是留给值得的人的。
他不配。
我悄悄睁开眼,看着窗外朦胧的月光。
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快点,再快一点。
我要尽快攒够离开的资本。
一天都不能再多待了。
我利用回娘家的机会,跟弟弟苏强说了我的想法。
苏强比我小几岁,脑子活络,上辈子就是村里最早出去闯荡的那一批。
这辈子,我想拉他一把,也让他帮我一把。
“姐,你想做买卖?”
苏强很惊讶,“这年头,割资本主义尾巴还没过去多久呢……”
“风向要变了,”我压低声音。
“你信姐,先从小的开始,去镇上人多的地方,卖点咱们山上的山货,或者编点小东西,亏不了。”
我把藏好的鸡蛋和大部分私房钱都塞给了他。
“这是启动的本钱,你先试试。”
“赚了,咱们姐弟俩分,赔了,就算姐的。”
苏强看着我,眼神复杂:“姐,你跟姐夫,是不是出啥事了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