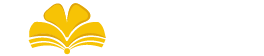像是听到了我的祈祷,上天留住了我的一个孩子。
医生说再待一周就可以出院了,我也能多去看他几次。
我蜷缩在病房的角落,指尖死死扣住保温箱的边缘,直到指节发痛,仍抵不过胸腔里翻涌的钝痛。
那个活下来的孩子到现在也只有巴掌大,浑身插满导管,像只小猫似的瘦弱可怜。
保温箱运行的声音此时格外刺耳,每一声都扎进我溃烂的伤口里。
林老爷子推门进来时,我正用额头抵着保温箱,试图用体温焐热冰冷的玻璃。
“小渝……”他苍老的声音里带着叹息,支票被轻轻放在床头,“林家欠你的。”
我盯着支票上龙飞凤舞的“林”字,忽然笑出声。
十年前沈家破产时,这张纸能买下我的一生,如今却连我孩子的半条命都赎不回。
“您知道吗?”我隔空抚摸着保温箱里微弱的起伏,“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呼吸的孩子直到咽气前还在攥我的手指。”
阴暗狭小的阁楼里,小小的生命脐带还连在我身体里,连哭都没哭一声。
像是命运对我恶毒的嘲讽。阁楼地板上的血渍早已干涸成褐色的疤,可我的心至今仍在滴血。
老管家来接我出院时,柳月正倚在林宅雕花铁门旁。她抚着尚未隆起的小腹,蔻丹鲜红如血:“姐姐真的要走?深哥说等你回来跪着给我系鞋带呢。”
我抱紧襁褓目不斜视地走过,任由她放肆大笑。
怀中的婴儿忽然啼哭起来,那声音细若游丝,却让我想起阁楼那夜。
宫缩的剧痛撕开皮肉时,我曾拼命捶打铁门:“求你们……让孩子活……”
可回应我的只有林深冰冷的声音穿透门板:“你推阿月时,怎么没想过今天?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好好学学规矩。”
机场贵宾室里,秘书将黑卡往我手里塞:“老爷子吩咐,您永远是……”
“林家没有永远。”我打断秘书的絮叨。
我推开那张卡,看着无名指上褪色的婚戒,心中五味杂陈,十年前林深不情不愿给我戴上它时,我的眼底映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期待。
只不过隔天就发现林深买来的只不过是赝品,他也索性坦白,真的对戒只属于他和柳月。
舷窗外云层翻涌如浪,我贴着婴儿冰凉的小脸轻哼摇篮曲。怀中突然传来微弱的抓挠,那是他第一次抓住我的衣襟。
“乖,妈妈带你去看看太阳。”
我轻轻地吻着孩子有些湿润的鼻尖,恍惚看见十五岁的林深在紫藤花架下回头。
少年衬衫上落满春日细碎的光,而他笑着递来的那枝丁香,只是命运的陷阱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