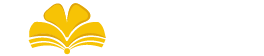我娘是人淡如菊的贤妃。
她不愿我和三姐姐争抢驸马,斥责我失了体面。
也不让我做爹爹的贴心女儿,说我是巧言令色。
于是,我丢了好驸马,也失去了爹爹的欢心,被迫下嫁给京中的浪荡子弟。
幸好婚后我与夫君相敬如宾,弟弟却因遭受新君猜疑被囚禁。
破天荒的,阿娘这回没有置身事外了,却把我和夫君都拉下了水。
毒酒一杯穿肠烂肚,再睁眼,我回到了赐婚的这一日。
1
“皇三女元婌毓质淑慎,抚远将军之子褚越忠正廉隅,朕今日就为你二人赐婚。”
宴会上,父皇刚刚将这话说出口,母妃就大喊不可,这时我才发现她也重生了。
上辈子她对我的婚事不闻不问,看着三皇姐嫁给了我的意中人,说是为了姐妹和睦不让我争,又极力赞同父皇把我嫁给落没勋贵之家,告诫我莫要贪图享乐失了风骨。
我本以为她一生都没有在意的事了,直到弟弟被囚,她又劝说我夫君造反,却遭惨败收尾。
临死前,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后悔,说如果当初让我嫁给褚越,而不是那个浪荡公子哥该有多好。
可世间事没有如果。
“贤妃此言何意啊?”
眼看父皇面露不悦,母妃赶紧解释道:“徽宁她倾慕褚小公子已久,这事皇上你也是知道的。而且,徽宁还做了好些荷包绣帕要送给禇公子呢,那鸳鸯戏水可是费工夫,我看她日缝夜缝的,这一番心意,陛下怎好辜负了。”
我脸颊热热的,背也僵直了,在场的命妇皇亲无不窃窃私语,父皇的脸色也不好看。
眼见场面冷了下来,三皇姐却笑出了声:“难为六妹妹惦记着褚越,只是妹妹尚未出阁便这般急切,可知道廉耻二字如何写吗?”
“够了!”茶盏碎裂,君王雷霆之怒让众人都跪了下来,“朕也为徽宁择了一门亲事,是安阳郡主之子,郡主已然应允,徽宁,你怎么说?”
“儿臣谢父皇隆恩!”
我立马起身谢恩,母妃目瞪口呆的看着我,接着又做出一副为难至极的表情,道:“臣妾也是为了徽宁着想,安阳郡主家不过空有个名头,在前朝也说不上话,徽宁怎能嫁给她的儿子?”
“贤妃娘娘不是人淡如菊吗,怎么这会儿也开始在乎这些东西了?”
母妃被三皇姐拂了面子,脸上不悦,正要开口再辩,却被父皇喝止。
“贤妃,你可还记得今日是朕的寿宴,谁准你如此藐视朕,忤逆朕!”
母妃瘪了瘪嘴,“臣妾是不如皇后娘娘处处顺从您,臣妾的女儿自然也不如三公主能讨您高兴。”
瞧着她这是又要拉我下水,我当即出座,表明自己有一支长袖舞已苦练多日,正要献上为父皇祝寿。
罗衣翻飞,红袖蹁跹,舞毕在坐众人无不惊艳,唯母妃兴致缺缺。
父皇斜睨了眼母妃,笑道:“徽宁如此懂事,朕心甚慰。”
2
宴席散了后,我被母妃叫到寝宫罚跪。
板子一下下落在身上,母妃坐在上首,怒道:“你可认错?”
“儿臣顺从父皇心意,不知何错之有?”
我不停呼痛,然而脸颊上的泪水并不能让她心软半分。
“我与你说过多次,我们家族只有后宫的女人,没有前朝的男人,你可记得?”
“自然记得。”
“既如此,你为何不跟你父皇抗争,你不争就要嫁给那个浪荡公子,你不争你弟弟以后就无人拥护,你不争,让我们母子怎么办?”
“母妃明明说过,要让弟弟做个尊贵王爷,既然如此,儿臣争与不争有何分别?”
听闻此话,她先是诧异,而后恍然大悟般,“你也回来了是不是?”
“儿臣不明白母妃此言何意。”
许是我骗过了她,也许是她自以为受天命眷顾的只能是她一人,沉默过后,她还是选择继续劝说我:“褚家有兵权,那那安阳郡主家有什么?以后太子登基,必定对我们不利,若不自保,我们可就完了。”
“太子哥哥霁月光风,若非我们不安分,他又怎会对我们不利,母妃多虑了。”
“六公主怎能如此对贤妃说话!如此不孝不悌的话,怎能出自公主之口?”
还不等母妃斥责我,闻讯赶来的兰嫔就先出口定了我的罪,她一向唯母妃马首是瞻,更是一昧护着她。
“是儿臣的不是,为免母亲烦扰,儿臣自个儿回宫思过。”
我挣扎着站起来,没有一个人来扶我,我回头看向她们,正义凛然,丝毫不觉得自己错了的样子,再次失望,自个儿一瘸一拐地离开。
3
鬼使神差地,我来到了弟弟的居所外,里头朗朗书声,声音虽稚气却叫人却不忍打扰。
“姐姐!”
小小人儿扭头发现了我,一下便将书本丢开,跑到我跟前。
“咦?六姐姐脸色怎如此苍白?可要请个太医瞧瞧?”
“不必了。”我强颜欢笑,“鸿瞻今日如此用功,母妃见着定觉欣慰。”
谁知我话刚说话,他便低下头,小脸上满是委屈,“母妃已许久不来看我了,姐姐,你说母妃是不是不疼我?”
怎么会呢?母妃可是为了鸿瞻的命,不惜置我于死地。
“母妃最疼鸿瞻了,你好好用功,过几日母妃定来看你。”
可这小人儿鬼灵精般,就是不信,缠我缠得紧,我正担心被他看见我背上的伤,冷不丁地,一件披风落在身上,我回头一看,却是褚越。
见着他,鸿瞻便挤眉弄眼地跑掉,不用问,也知是误会了。
“禇公子怎么在这儿?”
“臣应三公主之邀入宫宴饮。”他为我系上带子,温声道,“这遭没遂了贤妃娘娘的心,害公主挨了打,原是我对不起你。”
“还没恭贺褚公子,得偿所愿。”
“你明知道我心里只有你,何苦说这话来讽刺我?”
我笑了:“谈何讽刺?你与我青梅竹马,当初父皇也是属意你做我的驸马,可是你一头勾着三皇姐,一头又勾着我,两头下注,我今日如此,纵有母妃的缘故,又何尝不是拜你所赐?”
见他愕然,我又道:“可木已成舟,三皇姐是皇后所出,你选了她倒也不亏,不用来我这儿假惺惺的了,希望你以后永远别后悔。”
他卸下那温润君子的伪装,笑得坦然:“徽宁妹妹既看穿了我,我无话可说,如今公主应下的婚事也不算太差,往后,愿卿珍重。”
他拂袖离去,留我在原地,许是伤势过重,我感觉眼前一阵眩晕,晕倒前,我揪住假山后头一片青绿衣角,“我知道你在这儿偷听,求你唤个宫女将我扶回去,我,我不计较此事……”
4
醒来时,眼前便是薛衡的脸,看着他身上那青绿袍子我便明白了一切。
他是安阳郡主独子,我将来的驸马,做起伺候人的活计却不含糊,我看着他扶我坐起,端着药碗,小心翼翼的样子,仿佛回到上辈子。
最初的时候我是不愿嫁他的,他说要对我负责,便总哄着我。
他同我说遇仙楼的饭菜京城首屈一指,我不肯理睬他,他便三不五时索唤送上门来。
后来我与他熟稔些,话也说的多了,他便同我讲起京城的趣闻,我出嫁前不曾踏出皇宫半步,对这些自是觉得新奇,我们一同泛舟汴河,闲时投壶捶丸,倒也夫妻和乐。
若不是后头那件事,我们也能携手共度一生吧。
想到这儿,我眼角落下泪来。
他见我哭了,顿时手忙脚乱,“公主莫要伤心,公主若是不愿意嫁我,我自会和陛下说是我混账,不配迎娶公主,我皮实,挨顿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“可我已经和父皇说了,愿意嫁你,若你不娶,我可如何是好?”
见他愣了神,我更想逗他,“公子丰神俊朗,进退有度,可知是良配,徽宁心向往之,不知公子可愿娶我?”
我见他涨红了脸,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个可字,笑意愈发浓。
“背上好疼。”
我勾了勾他的手指,满脸委屈。
“我这就去给你找太医。”
他慌忙放下药碗就要出去,却被我拉住。
“母妃生了气,将我殿内宫女都撤走了,你若也走了,我岂不是一个人待着,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。你先别走,帮我擦些伤药可好?”
刚开始,他还不肯,可奈不住我的央求,还是替我解了衣衫。
“贤妃娘娘下手可真重,这还是亲娘吗?”
他一边替我擦药,一边吹着。
不知何时,我沉沉进入梦乡,窗外雨打芭蕉,风声萧萧,一片凄凉。
5
许是伤口没有妥善处理,夜里我发了热,薛衡不敢耽误我的病情,将太医院正背了过来,据说是嫌这老头子走路太慢,却将人都颠吐了。
此事还惊动了父皇母后,我醒时,宫殿里挤满了人。
皇后满怀关切,她到底是嫡母,对待我们这些子女素来温和。
父皇也是一脸担心,前些时日,因我听从母妃的话不再与父皇亲近,可到底血溶于水,我生了病他比谁都关心。
唯有母妃,坐在一旁的椅子上,见我醒了,她幽幽开口:“臣妾就说公主没事,皇上还硬是将臣妾唤来,再说了臣妾也不是故意要责打公主的。”
“是啊,姐姐也是慈母心肠,盼着公主好罢了,怎知公主反倒不领情。”
兰嫔这话简直要将我气笑了,她们一唱一和,合着是我不对了,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?
“贤妃,你把亲生女儿打成这样,丝毫没有愧疚之心吗?”
眼见着父皇发怒,母妃嘴巴嘟嘟,委屈道:“陛下如此说,臣妾百口莫辩。”
“药熬好了!”
薛衡捧着药碗,坐在我床头,及时将这茬岔了过去。
那药苦得难以入口,我每喝一口都要含着蜜饯才能下咽,他见此不由红了眼眶。
“贤妃娘娘,薛衡是晚辈,又是外臣,本不该置喙,但还望您今后对公主好些,这样的苦她本不必吃的。”
屋内静了一瞬,我拉了拉薛衡的手,示意他慎言。
怎料母妃却跟没听见他的话似的,自顾自说道:“陛下,臣妾看着薛衡和徽宁,好似想起我们从前的时光,墙头马上遥相顾,一见知君即断肠,臣妾与陛下于少年时相遇,心意相通,就如同这般。”
她念这段唱词时,脸上满是娇羞,岁月匆匆,在她眼角留下细纹,早没了少女的年轻容颜。
“贤妃,你如今几岁了,还在说这种痴话?”
母妃嘟着嘴,父皇的话倒让她更委屈了。
“陛下,薛衡有一不情之请,宫中侍女都被贤妃调走,怕是无人照顾公主,臣自请留在宫中,待公主伤愈后再出宫。”
赐婚本已过了明路,这倒是无妨,父皇刚刚应下,母妃却又不肯了。
“未婚男女,久居一室,成何体统,何况这桩婚事,臣妾不愿。”
“朕还未追究你的过错,何况你刚才不还说薛衡和徽宁如我们年少时一般吗?”
“臣妾是一时昏了头。”母妃狡辩着,满是不服气,“我看褚越年少有为,他和徽宁才是天生一对儿呢。”
“母妃慎言!”
我挣扎着从榻上爬了起来,哑着嗓子说道,“褚越是皇姐的夫婿,与我何干,反而儿臣观薛衡人品贵重,可堪托付,这都是父皇眼光独到,为女儿着想。”
听我此言,父皇由怒转喜,“徽宁孝顺贴心,朕这些女儿中也是数得上的了,你这些日子好好养病,贤妃也不必来看了,若是无事可做,便抄抄经书修身养性吧。”
母妃瞪着父皇,不言语,眼神中透露着不服气。
父皇早已习惯了似的,不再看她,又安慰嘱咐我一番后,将人都轰走了。
殿中又剩下我和薛衡两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