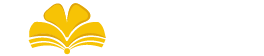奸相张兆文权势滔天,深得皇帝信任。
他一句谗言,我宋府便家破人亡。
一夜之间,我从清流贵女沦为逆贼之女。
再后来,我成了张兆文身边人人可轻贱的小妾,日夜受他磋磨。
他喝醉后抱着我深情求问:“莺莺,你爱我吗?”
我笑而不语,袖中剑抵在他的心脏。
1
“你就是京城才女宋莺莺?看来也不过如此。”
张兆文戏谑地看着我。
似笑非笑眼,像是一眼就能把人看透。
薄唇无情,唇角的弧度十分玩味。
我之前处于深闺,只在游猎会上遥遥见过他一眼,爹爹说,他奢侈僭逼,蝇营狗苟,手里有很多酷吏,手腕下作狠辣,不是好相与的。
但爹爹没说,他有异族血统,长的是一双绿眼睛。
对着那双猫咪似的眼,我一下背后炸起汗毛来,我能感觉到周遭的人都在看我,纵然在张兆文的压力下无人言语,但是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。
“宋太傅一生清流,为官为人都是顶上层的,怎么嫡女如此不要脸面,竟然自己到宰相府上求做小妾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,双膝跪下,向着张兆文行了一个大礼:
“宋家嫡次女宋莺莺,心悦大人已久,听闻大人在此举办赏樱会求娶贵女,特此前来,求嫁大人。”
张兆文有一身的通体文官气派,要是不看他那双眼睛,不知道他平日里都做什么肮脏事,定然会以为他是好人家读书出身的文人,但只要对上那双眼睛,那眼睛里的肃杀与沉默,充满血与刀影。
“你一个女儿家,怎么能自己给自己订婚事,多不体面,你爹娘呢?”
张兆文左揽一个美娇娘,右持酒杯,风流浪荡,是在故意折辱我。
我爹宋太傅连夜下狱,受三木酷刑,花甲之年饱受折磨,不就是拜他谗言所赐?我娘闻讯头风发作,大病不起,随父亲去了,不也是拜他所赐?
“说到巧意侍奉,我这既有会唱曲儿跳舞的美人,也有床榻之上颇有乐趣的美人;说到正室贵女,据我所知,莺莺姑娘如今已是布衣之身,做我的正室,似乎有些不妥当。”
张兆文说着,竟然在大堂之上拉过一旁的歌姬揉捏,伤风败俗,但无一人敢制止他。
众目睽睽中,我面上不动声色,但食指的指尖已经掐入掌心,疼痛让我清醒,更让我明白,张兆文小心谨慎,断不可能轻易收我入府。
这场赏樱会是当今皇上眼前最红的丞相张兆文所举办的,整个东京城的贵族都来了,其中不乏父亲昔日学生和旧时好友,当着他们的面,我将发上的簪子拔下,挽好的精致发髻顺势滑下,我长发捶地,以簪抵颈。
“我自小心悦大人,若大人愿意收我入府,我甘愿为妾,与宋家断绝关系,从此只是大人的人。若大人不允,我血溅张府,以命证明我对大人的一片痴心!”
众人惊呼声中,我将自己掌心掐出血痕。
2
“你这又是何必?血溅宰相府,亏你说得出来。爹爹刚去了,娘也随父亲离开了,如果我再失去你这么个妹妹,你让我如何是好?”
姐姐的话很轻,她自幼身体不好,又在孕中,讲话都有气无力,纵然穿金戴银也没有用,红珊瑚步摇都衬不出她脸颊的一抹红色。
我抬头,对上她的目光。那目光忧郁哀愁。我知道姐姐作为贵妃,又刚怀孕,月份不大,宫中大小事,都有她烦的。
更何况陛下听信了张兆文的谗言,将爹爹连同数人以谋反案下狱,甚至没有经过大理寺的手,都是张兆文一手处置。
张兆文下手极狠,从下狱拷打到处决,不过是一个月的事情,我未曾见爹爹最后一面。
爹爹死的那天,三千太学生阶前下跪,求情的折子不计其数。
那日是罕见的日食,天象大凶,皇帝没有理会三千太学生的求情,也没有见怀着身孕跪在殿前的我姐姐。
世人都说,宦官当道,清流下狱,可悲可叹。我爹爹一生清廉,学的是圣贤之书,习的是办有用之事,却死于党同伐异之争,死于玩弄权术的奸相之手。
同族放归田里,为官之人终身罢黜。蒙姐姐之恩,我免去军妓的处罚,从此为布衣之身。
可我不甘心!我痛!
痛爹爹清明之人,被陷害,死的不明不白。
痛姐姐有孕之身,被连累,整日不得安宁。
痛娘亲该享福的年纪,被噩耗打击,随父亲去了。
宋家嫡脉凋零,养我十八年,无以为报。
我低下头,不让姐姐看到我眼眶里的泪水,向姐姐一拜:
“莺莺心悦张相,愿意自请为妾,今日在此立誓,从此我宋莺莺与宋家一刀两断,再无瓜葛。”
手腕上一痛,是姐姐不顾贵妃身份扑下来,抓住我的手腕:
“莺莺!你同我讲实话,你是真爱慕张相,愿意当他的妾室吗?宋家只剩下你我二人了,你切莫做傻事!若你出了事,你让姐姐怎么办?”
姐姐慌乱之中,步摇坠落于地,清脆一声,犹如我与姐姐的关系。
姐姐,事已至此,我别无选择。
我望着她布满红血丝的眼睛,抹去她眼角的泪珠,将她扶起,再次向她一拜:
“长姐在上,受莺莺一拜,从此山长水远,长姐多加保重。”
我转身离开金碧堂皇却空寂寂寞的贵妃殿,长姐被众多侍女搀扶着,在身后用力喊我:
“莺莺!你莫做傻事啊!”
我听了,不自觉就落下泪来,但不曾回头。
阿姐,阿姐,他们从小就说我是个聪慧的。
怎么就你总叫我傻丫头,总是护我周全呢?
3
凭为情自杀那场闹剧,我闻名东京,入了宰相府。
张兆文看似轻佻,其实从不近我。
他不信我。
他把我的居所安排在暗室旁边,我爹爹的谋反之案还有些连带之人,有些小鱼小虾需要处理,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甚至是凌晨,我都常常听到撕心裂肺的嚎叫,和战战兢兢的求饶。
刑具作用于皮肉上的声音常让我做噩梦,我常常梦见爹爹惨死狱中,尸体皮开肉绽。
梦见张兆文的黑手套上全是血,他冷漠而狡诈,看我的眼神似笑非笑,如寒芒在背,像极了绿眼北极狐。
转眼入了冬,许是东京严寒,死的人变多了。
我的近身侍女常蕊告诉我,每日寅时打过更,张兆文用于拷打他人的暗室就会拖出一堆尸体,个个遍体鳞伤,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,血迹从暗室里往外蔓延,渗透了夜里累的雪。
暗室里的酷吏武功都十分高强,她不敢靠近,远远地尾随着,顺着雪上尸体曳拽的痕迹,跟到了张府外荒山的埋尸处,竟然找到了三伯家表公子的尸首。
不顾她的阻拦,我执意要去看看。
严寒也难以遮掩血腥味,尸臭阵阵引人作呕,偌大一个尸坑,面目都难以辨认,表哥身上没有一块好肉,但腰带上香囊却是我亲手绣的。
他们搜刮完了表哥身上所有的富贵物件,没拿这个拙劣的香囊。
三伯家的表公子,人人都说是富贵闲人,三伯父想让他考取功名,他却听戏看舞斗蛐蛐儿,天天和我上街玩闹。
我最不上进的哥哥,却没有归田离京和我们嫡系一脉撇开干系,而是上书给爹爹求情,落得个乱葬岗里埋了的下场。
乱葬岗里尸体不少,生前都受了不少苦。
我想着那些人里有谁?谁家亲戚,谁家儿郎?想着心就痛起来。
4
张兆文仍然不近我,他大请宾客吃冬日宴之日,我不请自到。
张兆文满眼玩味,他所宴请的也都是阉党一派,他们望我的眼神像是要在我身上剜下一块肉来。
“贵女何意?我们阉党聚会,贵女怎么不请自到,难道是怕我们聚会乏味,来给我们献舞作乐?”
张兆文的尾音上挑,语气暧昧,眼神却如刀刃般锋利。
我爹爹已经被处决,我已失去贵女身份,他话语间将我比作舞姬,是有意折辱我。
堂下笑声四起。
我乖顺地道:“正是如此。各位大人饮酒商谈,岂能缺了舞蹈?小女子愿意自请伴舞。”
张兆文的眼神中一闪而过错愕,我走到宴席中央,正准备起舞,熟料张兆文抬手制止了我:
“不急。宋娘子才女之名响彻京城,跳舞之事应该难不倒你。只是在场诸位大人都见惯了跳舞,不如宋娘子换上和她们一样的绿舞衣?”
他所说的是官妓们所穿的绿舞衣,下贱如妓才穿这样纯的绿色。
我一个清白女儿家没名没分进入张府,已经是丢脸至极;给害父亲下狱的仇人伴舞,更是折辱。
他的目光如鹰隼在我面上巡视,我掐着掌心的手一松:“大人有命,小女子岂敢不从。”
我换上官妓们所穿的绿舞衣,在席中央作舞,衣袂若飞,轻盈飘逸,舞衣清透,透出皮肤如雪。
觥筹交错间,暖香阵阵,张兆文看我的眼神耐人寻味。
我没学过讨人欢喜的舞蹈,一板一眼间都不够柔软。
我干脆脱下鞋子,光脚踩在地毯上,脚踝上的脚铃随着我的舞步而轻响,我边舞蹈边靠近张兆文,行到几前,我将张兆文桌前的酒一饮而尽,踮起脚尖吻上张兆文的唇。
我第一次接吻,不知是不是我错觉,他身上有股血腥味,铁锈味其实是人命味。
我刚想抽身而出,张兆文环住我的腰肢将我一揽,一旋,眨眼间我就倒于几上,他用舌尖撬开我的齿关,与我共饮那酒液。
酒很烈很苦,张兆文的唇很凉。
他在我唇齿间攻城掠地。
“接吻是这样的,懂不懂,宋娘子?”
他的拇指按揉我的唇,拇指上有茧子。
5
我知道在场所有人,都将我与张兆文接吻看在眼里。那夜过后,我的名声将一败涂地。
但是那晚,张兆文终于进了我的房。
我从前以为这样事,是体己人之间的美事,我常想着元臻高中状元之后来我家提亲,我们三叩九拜,明媒正娶。
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。多好。
但是我等不起了,我等不起元臻。
那个身上总有淡淡书墨香味的白面书生,是与我青梅竹马,从小定情的郎君。如今他关在考场里,不知道外面已经变了天。
而如今上我榻的人,成了天下最最心狠手辣、最最奸诈刁滑的张兆文。
他看着清瘦,其实劲挺健壮,腰腹有力,床纬晃荡,极乐与痛苦交织,我的绿舞衣被他撕破,片片尽碎。
“如今是不是如了你的意?”我的指甲在他背上掐出印痕的时候,张兆文俯下身,在我耳边笑道:“清流之女,钟鸣鼎食之家,不过如此。”
晃荡间,我抓到他的黑手套,那上面的血痕吓了我一跳。
张兆文却像看到什么趣事一般,用指尖沾了血印在我唇上,舔咬我的唇:“怕吗?”
我想起乱葬岗里的表哥,他遍体鳞伤,被抛尸野外,只能当孤魂野鬼,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我咬破了自己的下唇,道:“不怕。”
张兆文的手如湿滑的蛇游走,眼神如刁蛮的狐奸诈,床榻之间,他身上的血腥味似乎也浸透了我,我的泪已经在之前的千百次里哭干了,只是麻木地环抱着他劲瘦的腰身。
他碧绿的眼睛星子透亮,说出来的话却是酷吏所言:
“不怕才好,我身边的女人,不能怕死人。”
张兆文走后,常蕊进来给我擦洗,青青紫紫,十分可怖。
常蕊用布擦拭我身上的血迹,血迹早在几次欢好时干涸,不是很好去除,常蕊擦着擦着就落下泪来:“我们小姐也是千宠万爱长大的,怎会,怎会……”
我伸手捂住她的口,冲她摇了摇头。
“没关系,也不是我的血,寄人篱下,有些话,莫说。”我疲惫地靠在纬帐上,叮嘱常蕊。
常蕊为我擦拭着身体,我的思绪渐渐沉下去,眼前仿佛出现爹爹冲我笑的样子:
“我给你带了桂花糕,是你最喜欢你那家碧春坊。”
我穿着未嫁女儿装,上去欢欢喜喜地揽住了爹爹的手:“还是爹爹记着莺莺。”
站在旁边的母亲也走过来挽住我的手:“莺莺真是个贪吃鬼。”
还是姐姐最好,姐姐开口护我:“吃个桂花糕嘛,小女儿家,贪嘴……”
红衣状元郎冲我伸出手,元臻神采奕奕,清俊依旧:
“莺莺,等我下了学,我陪你去放风筝,好不好?”
好……当然好……
我彻底昏睡过去,甚至不知道颊边留下泪痕。
6
张兆文纳我为妾。
这个屈辱刺入心扉,但我早已千疮百孔。
也算是我求来的,不是么?
婚轿从侧门入,甚至没有什么仆从,我潦潦草草地嫁了张兆文,甚至没有聘礼。
姐姐给我写了信,我看了,但没回。
倘若我计划失败,张兆文也不会连累姐姐。
元臻进考场前告诉我:“莺莺,等我高中状元我就八抬大轿,三书六聘,迎你入门,做我元家的正妻。”
他拉着我的手,少年人发誓的样子格外认真。我抚平他衣袖上的褶皱,微红了脸应他。
那时候爹爹和娘亲就站在一旁,看我俩说话的样子满是欣慰。
爹爹多年太傅,桃李满天下,元臻是他最看重的学生。
爹爹说他会中的,中了状元,就娶我当正妻。
爹爹说话,向来准的。
只是我没福分。
我跪了张兆文列祖列宗,真真正正,入了张府。
成了阉党的妾。
大婚那晚,明烛高照,张兆文仍然没给我换居所,旁边暗室里的嚎叫此起彼伏,血腥味和红蜡烛相得益彰,本就是不吉利的婚,不是么。
我等了张兆文半宿,婚服沉重,滴水未进,又饥又困。
张兆文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了一阵冷风,吹得我一下惊醒。
他黑色劲服,落满了雪的金绣披风,仍然是黑手套。只是这次黑手套被血浸得甚至发红,血珠颗颗分明,滴到了我大婚的地毯上。
很重,很浓的血腥味。
我穿着婚服,但他没有。
张兆文解开披风,将外衣脱下:“今日有个重要人物需要处理。来迟了。”
他似是在与我解释。
我不在意地斟了一杯酒:“大人辛苦了,请用这杯酒,暖暖身子吧。”
张兆文定定望了我许久,碧绿瞳孔里透出探究的意味,我向他举杯,张兆文一手拉过我的手腕,一手环过我的腰肢,饮入整杯酒的同时,又吻上了我。
他将酒液渡入我口中,我无奈咽下。
他怀疑我在酒中下毒?
我未曾言语,又被张兆文堵住口舌,他的手即将爬上我的大腿,我出言阻止他:“能不能脱掉手套?”
“起码这是我们大婚,夫君。”我乖顺地说道。
他沉默片刻,将两只黑手套脱下来,甩到地毯上。
沉重而腥臭的血点溅到了我的鞋面,张兆文将我打横抱起,摔到了床榻上,附身压下来。
元臻身上都是书墨气息,而张兆文的血腥味,可怖难闻。
“明日科举就结束了。听闻你和元家那个小崽子有私情?”